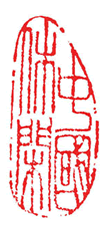
欢迎进入中国休闲研究网站
Welcome to the Website of Chinese Leisure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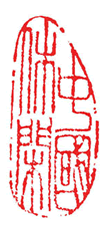 |
欢迎进入中国休闲研究网站Welcome to the Website of Chinese Leisure Studies |
君特•菲伽尔教授谈“何谓休闲”?
(君特•菲伽尔:德国哲学家,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研究重点是诠释学、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史。2003年至2015年间,担任马丁•海德格尔学会主席。2024 年1月19日去世,享年74岁。)
君特•菲伽尔教授
"为休闲研究辩护" 任何选择休闲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都无需担心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那些偶尔听到的对人文学科或文化研究的无意义的怀疑并不会在休闲方面出现。至少,我们这些希望在新成立的合作研究中心处理休闲问题的人是这样想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话题都很受欢迎,一直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没有人怀疑休闲的意义的必要性,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都需要休闲或更多的休闲,我们怀念休闲,通常,我们都能说出为什么需要休闲。 越来越紧凑的日程安排、频繁出差的负担、与电子媒体相关的持续通讯的需求、同时处理几件勉强可以应付的事情(也可称为多任务处理)——这些都是当代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常常以对休闲的渴望来回应这些方方面面。 以“人们终于应该再次……”开头的句子就表明了这种愿望。我们所希望的绝不仅仅是“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希望是终于有机会能够再次安静地工作,终于能够再次毫无压力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件事情中,并且能够正确地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全神贯注地完成手头的任务,而不是因为下一项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而半途而废或注意力不集中。 对休闲的渴望不仅影响着现代的工作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且还影响着工作生活本身。在这方面,这种欲望也促使我们思考新的、不同形式的职业活动。对休闲或更多休闲的渴望与当代的其他渴望或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人们深信食品工业的有毒产品和劣质产品应被对动物和人类友好的、以地方特色为主的食品所取代,或者怀疑度假之旅是否真的必须去加勒比海或巴塔哥尼亚。 这还包括认识到,高质量的和相应的可持续的消费品最终是更好的,甚至是更便宜的。做正确的事与意识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希望身在其中而不是无处不在的愿望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减速是解药吗?" 在大众的非虚构作品和科学研究中,已经对改变生活态度的这种氛围方面进行过多次思考和阐述,而且也并不缺乏对如何做的纲领性思考。 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公众辩论中提出的“减速”概念尤其成功。这一概念说服并激励了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艺术展:如果罗萨和在他之前的法国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试图证明加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那么减速似乎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性的时代特征首先是工业革命,其灾难性和危机四伏的发展决定了二十世纪,也决定了我们的时代。 一个世纪以来,从加速的角度来看,现代性变得越来越快,这种加速度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现在显然需要刹车;变革的步伐必须放慢,这样现代世界才是可以承受的。 然而,必须允许有人怀疑这是否属实。毫无疑问,维利里奥和罗萨所诊断的加速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是否能像罗萨所说的那样,仅仅从加速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这一点值得商榷。 例如,所谓数字革命的问题不仅在于它“越来越快”,还在于它“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又与“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密集”联系在一起。我们面临着如此丰富的数据和信息,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控制它们,用现代性最敏锐的诊断者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话说,世界“再次变得无限”。 由于面对这种复杂性,控制已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人类创造的领域,在那些旨在提供世界全貌的领域——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应该在有限的、可控的范围内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而不是继续迷失在渐进的技术控制甚至自然控制的妄想中。放慢速度可能意味着降低效率、减少劳累、减少自我毁灭,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同于现代早期的征服和控制方式。如果问题不在于速度,而在于“不同”,那么,解决问题的措施就不仅仅在于“较慢”。 "什么是休闲?" 意识到事情必须有所不同时,不应强调传播。我们不应重复早先现代性的改造世界和改造生活的姿态,要求我们对生活和活动的理解发生全球性的、同时也可能是快速的变化。我们最好满足于在小范围内、在个人生活和行动的具体细节上进行变革的可能性,而不必担心其他人是否“已经”在做同样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如何能够并希望在总体上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休闲的概念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关键概念。虽然我们多少知道休闲是什么,即我们对休闲有一定的概念,虽然并不精确。而当我们试图用语言表达这种想法时,通常会变得很困难。 就像我们对许多事物都有一定的认识一样,休闲也不是那么容易描述和理解的。由此可见,休闲是一个哲学问题。休闲现象包括我想称之为奥古斯丁测试的内容:当被问及“休闲是什么”时,它是一种无法确定和描述的已知事物。人们必须努力澄清对想要了解的事物的预先理解,并在这个意义上,询问在获得不同的行动态度时,在渴望休闲或更多休闲的指导下,人们可以合理地渴望或想要什么。这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科学方法或概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休闲的方式来看待它,以我们谈论休闲的方式来看待它,甚至不想去确定甚至定义它。 为了对休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必须关注人们是如何谈论休闲的,哪些术语和描述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哪些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这样,在各种界定和划分的结构中,就会形成对休闲的初步理解。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我们如何将“休闲”一词与我们的经历联系起来,来形象地理解这种理解。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说自己休闲、充满休闲或只是休闲?就休闲的界定而言,首先要注意的是,休闲并不等同于空闲时间。 休闲是一个人不必工作的时间;它是由工作时间决定的,因此也是由劳动决定的。休闲将工作排除在外,但又允许工作作为一种排除而更加存在,因此,一个人如何度过休闲时间也可能完全取决于对工作的态度。休闲并不那么排斥工作。人们可以在休闲时工作,但工作会因休闲而改变。此外,有些形式的工作只能在休闲中展开。各种创造性工作都需要休闲才能取得成功。 但是,休闲并不局限于这种形式的工作。长时间的散步和远足是这类活动的必选项目。休闲不是休闲时间,但它可以充实休闲时间,并赋予其平淡的标准乐趣所不具备的意义。如果休闲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有意义的满足,它就会变成空闲;用拉丁语来说,它不再是otium,而是otiositas。休闲可以让人暂时放松,甚至感到愉悦,但长此以往,休闲就会变成令人痛苦的无法实现的时间,从而产生厌倦。 单纯的闲置是“无所作为”,而休闲总是有为的,但你在休闲时做的事情又是如何因休闲而改变的呢?休闲时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一个人的行为是自由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因此,休闲本质上包含着自由。只要一项活动是为了养活自己、谋生或发展事业,它就会面临成功的压力,一旦感受到这种压力,无论多么轻微,这项活动就无法自由展开。只有在没有内部或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才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从而使这项事业在本质上与你息息相关。 "休闲与自由" 这也许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闲暇中看到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实现/εὐδαιμονία的原因之一。如果说休闲是一种满足,是一种尽管对生活持开放态度但却一无所缺的状态。休闲并不在所有方面都排斥意志,但它与由意志决定的生活不相容,因此也往往与由权力决定的生活不相容,因为权力是以优越和统治为导向的,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把与权力和荣誉承认有关的政治生活理解为休闲生活的原因。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属于休闲的幸福是无法带来的,当然也不是被迫的;它是自发的,而且只有当一个人让他人和他必须做的事情存在时才能产生。这并不意味着逆来顺受的被动,也不意味着冷漠无情,而是一种警觉的开放心态,在这种心态中,人们可以参与其中,从而自在地生活。宁静是休闲的一部分;拥有闲暇的人可以顺其自然,从而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 在这种放松的态度中,没有什么是勉强的。仓促、匆忙、紧张和急切都与休闲格格不入。因此,在休闲中做事总是意味着没有时间压力,更准确地说,期望的压力、必须实现目标的压力或意志的压力,即时间的压力。在休闲中,没有什么是紧迫的,没有什么是匆忙的;你有时间,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休闲并不包括有时间。 当你追求目标、雄心勃勃或权力意识强烈时,当你有期望要实现或有不可避免的事情要做时,你也可以有时间。在需要做的事情完成之前,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不管是计算出来的还是估算出来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时间的独裁特性。即使是有时间的人,也会有时间压力,只是这种压力暂时放松了,因而变得温和了一些。 而休闲则不同。只要你有休闲去做某件事,时间就不再起作用。当然,时间并没有停止,只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暂停了。你可能知道,你并没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去做某件事,也许只有几天或几小时,但如果这几天或几小时是充实的,那么衡量天数或小时的标准就不适用了。 人不会被时间的流逝所左右,因此可以从容地对待事物;事物就在那里,人与它同在,为它而在。你可以让它封存。但这意味着,休闲也总是沉思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将闲暇定义为θεωρία的重要时刻,即不受任何实践或政治约束的哲学沉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相反,在休闲中进行的每一项活动也总是沉思的;一项活动可以是形成性的,也可以是完成性的;只要是在休闲中进行的,就不会强求解决。 在休闲中,你总是允许你所从事的事情得以实现。解决方案可以是开放的,可以是其他可能性的,包括不可预见的,不可预知的。例如,艺术家在休闲时创作的作品可能会让艺术家本人感到惊讶,而科学或哲学对话则可能会带来参与者都未曾预料到的见解。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一个人产生了新的想法,或者他研究了很久的东西突然变得通俗易懂,而不需要他做任何努力。在休闲中,它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你可以让它自生自灭。 重复一遍,时间不会因休闲而终结。但它并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外部空间并不能保证休闲,反之,休闲也并不局限于专门设计为外部空间的空间。休闲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机场的候机大厅,在熙熙攘攘的旅途中,或者在城市中央的繁华广场上。然而,这只有在机场大厅或广场被视为休闲空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的空间是独立于其正常用途或与其相反的,是一个必须充满乐趣的逗留机会,即一个以满足、沉思、宁静和自由为特征的空间。那些使人无法沉思的地方,例如过于嘈杂、通风不畅或其他不适宜的地方,也不可能成为即兴的或新发现的沉思空间。 因此,有一些空间是专门为休闲而设计的。它们是作为休闲文化的建筑而出现的,或者是从休闲文化的指导思想发展而来的,例如桃山时代(1573-1603 年)日本茶文化的茶室和茶园。它依赖于可以找到、发现或创造的休闲空间。反过来,在空间性方面,休闲以一种特殊的、特别明显的方式具有空间性:休闲要么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空间,要么总是能找到自己的空间。它需要它的空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以一种特殊的、截然不同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空间体验,是一种允许或促成休闲意义上的逗留的空间体验。 在这种空间性中寻求休闲的特殊性,是大有可为的。休闲不只是自由,但自由——就像满足和宁静——也可以通过休闲以外的方式实现。一个人在任何行为中都是自由的,而在这些行为中本可以有其他实现方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是充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缺失任何基本的东西,无论个人可能缺失什么,需要注意什么,都是充实的。就其本身而言,宁静是一种态度,它可以在异常空闲的情况下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同可能性的并置是沉思的特点,这种并置也存在于思考该做什么的时候——当然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在这方面,每个行动的合理性都有沉思的时刻。 但是,在休闲中,自由、满足、宁静和沉思的理解、沉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空间上汇聚在一起。在一个允许、有利于或促成它们的空间范围内,它们一起出现在那里,就像在一束特别清晰的光线下,可以在它们的组合中得到体验和认识。 长期以来,“做”、“生产”和“结果”一直主导着人类生活的自我理解,与其将注意力集中在“做”、“生产”和“结果”上,不如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休闲”,即在“做”的可能性范围内体验“做”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地接近“做”,或多或少地接近“可能性的范围”。它表明,积极的生活属于一种超越“做”与“结果”的开放性。
(本文选自德国弗莱堡“荔”的微信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