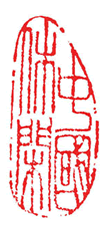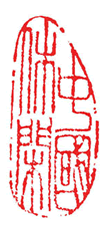于光远与中国休闲研究
宁泽群
北京联合大学现代休闲行为与旅游发展研究所
中国休闲研究的奠基者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去世,对于逝者最好的怀念,就是对他休闲思想的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意味着他所奠定的休闲理念的延续,而且意味着他的生命并没有随着物质实体的消失而终结。
于光远先生作为中国休闲研究的开拓者对过去二十年中国休闲研究所倾注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能够建立中国休闲研究学科特点,引导中国的休闲研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常常利用中国休闲年会的机会发表他的思想观点,每次在北京召开的年会他都会亲自出席。让人难以忘记的是,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休闲社会学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于光远先生以94岁高龄做轮椅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由他的秘书代为发言。可见他对休闲研究事业的重视。
为了缅怀于光远先生对中国休闲研究所作的贡献,对他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所发表的讲话和文献做了整理,以提供研究的方向性思路。
一、休闲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丰裕,进一步强化了工作是生活唯一目的的观念。正是由于人们囿于这种长期形成的对生活认知的偏差观念,休闲始终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被社会发展所忽视。我国在传统体制时期亦是如此。休闲娱乐在文革期间甚至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人们获得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的权力,但经济落后的状况和物质的匮乏,使得人们更关注的是物质的获取和丰裕,在追求效率的繁忙工作中,似乎已经忘却了“休闲”两字。
然而,于光远先生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全民皆商”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高度,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的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乐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休闲会使人们愉快,它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占到应有的地位。”由此,于光远先生在1996年提出的休闲与社会文明发展同步的观点,即未来社会是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在他为2007年中国休闲学术年会提供的书面讲话中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尽管一些国外学者也提出了有关未来是休闲社会的观点,但于光远所定义的“普遍有闲的社会”的内涵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休闲现象日益普遍的事实来定义的,而于光远则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人的全面解放的角度来定义的,即“闲”与文明是孪生姐妹。与许多将休闲与工作(劳动)相对立的西方学者不同,于光远先生更倾向于将休闲看作社会发展水平的范畴,它是用来划分自由生存(劳动)与不自由生存(劳动)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休闲与劳动是对立分离的,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使得人们不得不被迫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不自由的生存劳动,自由的休闲变成为了不自由劳动的对立状态;而在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相对充裕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满足,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自由支配的生存活动,劳动的不自由性质发生的变化,自由生存的活动(劳动)与休闲活动合为一体。这种活动体现出更好的创造力,成为了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社会发展从“有闲阶级的社会”走向“普遍有闲的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便成为了一种可能。于光远先生将这种未来社会的劳动称之为“乐生要素”,而不是“谋生手段”。
二、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休闲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人类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其关键在于它与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经这样强调过休闲的重要意义,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荷兰著名人类文化学者赫伊津哈更是将游戏称为人类文化的基础。奥地利著名哲学大师皮珀的名著《闲暇:文化的基础》则系统论述了休闲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创造是离不开休闲的。人只有在静思和默观的状态下,才会迸发出奇思妙想的灵感,才会获得某种真谛的领悟。于光远先生在《闲——最大最大的字眼》一文中列举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无不来自于休闲。因此,于光远先生告诫我们,“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一忙就容易烦,心情不得和平;一忙就很容易认识肤浅,不能自己研究问题,不能冷静思考,一忙就容易只顾得眼前,不能高瞻远瞩。”
实际上,休闲不仅仅与人类的智慧创造有关,它还伴随我们的一生。纵观人的从生到死的过程,我们与工作的联系仅仅体现在人的就业阶段,而休闲却伴随我们从牙牙学语到步履蹒跚。现代科学研究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休闲游戏对人的成长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游戏对儿童的智力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时期的游戏缺失与成年以后的幸福生活具有直接的相关性。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在一项对参与他研究的孩子们的长达30年的跟踪研究中表明发现,孩提时能将玩兴置为事物核心的人在30年后过着最为有趣和充实的生活。而老年人缺乏对自我生活中休闲活动的掌控与责任感,则与死亡率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都说明了休闲与人的一生的重要意义。
正因为如此,于光远在为2011年中国休闲学术年会致词中一再强调指出,“休闲的价值不言而喻,没有闲,人的自然成长都有问题。”然而,在我国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下,国人更多的是关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的享受。针对这一问题,于光远先生提出研究价值观的重要性。他指出,价值观“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在对各种社会实践进行评价时所持的观点。具体地说,就是什么样的社会目的,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去追求”,而“凡是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就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去奋斗的。”他强调,“富裕是幸福的基础,贫穷、困难当然是一种不幸,但富裕也并不就等于幸福。”可见,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享受生活。于光远先生认为,“什么叫享受呢?享受是指满足生存需要以上的生活内容,比生存高一等。”所以,“为了享受,不但要有享受的物质资料,同时还要有可以用来享受的一定的闲暇时间。”
正是这种基于这种追求真正幸福生活的理念,于光远先生提出创立“玩学”的思想,并自称自己是个“大玩家”。他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改为“人之初,性本玩”,并且,要“活到老,玩到老”。他自己提出了“玩学”的六个重要的方面,即1、“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2、“要玩得有文化”;3、“要有玩的文化”;4、“要研究玩的学术”;5、“掌握玩的技术”;6、“发展玩的艺术”。这一框架为我们搭建了休闲研究进一步探索的基本理论体系。
三、休闲行为的特征与层次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当国人从物质就能获得幸福生活的幻想中开始醒悟过来以后,休闲一词就从冷僻的陌生变成为一种时尚的表达。人们开始任意地引用它来为自己的各种娱乐行为做注解,以至于它几乎成为了一种工作之余随意利用的万能商标。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浮躁现象。因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休闲像任何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样,有着其辩证的多重内涵。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光远先生已经开始告诫人们,休闲并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的概念问题。他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中不仅强调了业余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区别,指出业余时间即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休闲时间则是业余时间内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而且,还强调了休闲具有各种不同类别的行为状态,我们不应该仅用休闲时间来理解休闲的复杂性。他指出,“闲”的状况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以是看和听,也可以是体育活动;它们可以是呆在家里,也可以是外出旅游;它们可以是一个人的独处行为,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的互动行为。因此,不能只讲“闲”的一般性,还需要研究“闲”的特殊性。他还特别指出了在中文中休闲的“休”字所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不做什么事的“休”(休息);一是不能闲着的“休”(休要闲着,即需要活动)。
正是由于休闲活动和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光远先生清醒地意识到休闲行为实际上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即休闲行为存在着健康和不健康的不同类别。因此,2009年,他在为当年的中国休闲学术年会的书面讲话中强调指出,“休闲是科学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一件最重要的“礼物”。它既可以成为人类“成长”的助推器,也可以因“闲”不当,而让人类沦为“魔鬼”。”这是于光远先生在告诫我们,忽略了休闲行为具有层次性的特性,就不能很好地利用休闲行为来发展和完善自我,相反,可能会毁灭自己。
关于休闲行为的层次性,国外休闲学者做过不少的理论探讨。其中,美国休闲学者J.B.纳什曾经就休闲行为层次性的这一特点,从道德角度做了排列等级,提出了一个休闲参与层次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比较好地解释了不同层次上的休闲行为对人的身心健康的不同作用和影响。他将休闲行为模式分为六个层级:最低层级纳什称为负层级,其表现为不良行为(如破坏公物等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反社会性质),次低层级是0层级,其表现为放纵行为(如酗酒等,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自我伤害),再上面的层极是第1层级,其表现为消磨时间行为(如被动地看电视等,这种行为属于被动消遣的休闲活动),再高的层级是第2层级,其表现为投入感情的参与行为(如歌迷、球迷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促进情感的交流),再高的层级是第3层级其表现为积极参与的行为(如旅游、跑步、演唱等,这时的行为个体是直接参与活动之中),最高层级是第4层级,其表现为创造性参与行为(如发明活动、艺术创造活动等,这种行为往往会使得行为者陶醉其中,实现身心舒缓、愉悦心情的作用)。
可见,休闲行为的不同层次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积极休闲可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消极休闲则可能毁灭我们的一生。这些都正是于光远先生希望我们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休闲产业的任务和目的问题
休闲产业及其发展,是休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服务于社会消费群体的多样性休闲活动的部门,休闲产业如何健康地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们生活质量提升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的重要基础。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光远先生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休闲产业的巨大商机和发展的复杂性。他指出,“由于今天休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休闲产业的市场就必然很大。同时人需要各式各样的休闲方式,休闲产业也就一定是包罗多种多样行业的产业。”“在今天,休闲和休闲业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十分复杂,因此对休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来考虑。”
21世纪以后,我国休闲产业及其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印证了于光远先生的这种远见卓识。不过,随之而来的产业高增长,也凸显出一些发展观念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导致我们更加关注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观念成为了我们的思维惯式,渗透在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新兴产业的潜在发展机会,就都盼望它能够成为GDP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以至于人们对待今天的休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持有这种观念,似乎休闲产业和旅游产业将成为房地产业、汽车业以后的新的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于是乎,完全不顾社会承载力的超载游客的拥挤数量,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休闲与旅游的资源开发项目都成为了新经济增长点的标志性指标,堂而皇之地在各种主流媒体上反复传播、复制和颂扬。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光远先生看到休闲产业大发展的同时,就已经对休闲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指出:“休闲业这个产业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满足人们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业当然要取得经济效益,否则休闲业不可能扩展起来,但休闲业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就是因为它能满足休闲、消遣这种社会需要。而要取得好的效益,就必须认真细致地研究这种需要。可是现在从事休闲业的人,往往不去研究“闲”这种现象,不去研究休闲、消遣这种生活方式,只考虑自己的财源,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地看法,应该纠正。”2000年,于光远先生在“休闲产业国际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再一次告诫我们,“休闲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人只看到开展休闲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研究休闲本身,比如说,只讲“假日经济”,而不多讲如何使人过好假日的生活,而后者应该是发展休闲产业的目的和基础。”
在当时,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告诫,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产业成长和发展的简明道理,即:一个产业的诞生与发展是要源自于这个社会的消费群体对这一类产品或服务的普遍需求,因而,产业应该以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来更好地满足这种社会需求,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是一个产业生存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而如果这个产业的生产者们只是一味单纯地追逐经济收益,甚至不惜以损害消费群体的权益为代价,那么,这个产业的发展必然是没有前景的。
由此可见,离开了对人的生活质量的服务目的,仅仅为了经济利益来发展休闲产业及其旅游产业,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真正发展。
结语:
休闲研究必然关注与社会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关注休闲行为的特征与层次性问题,以及休闲产业的任务和目的问题。这些是休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难以把握的问题。然而,早在20年前于光远先生就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识,我们回顾上面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一个思想者的睿智和对社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于光远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而我们对他的最好怀念,就是让这些闪光的理念得以传承与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