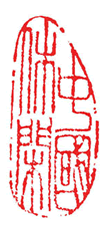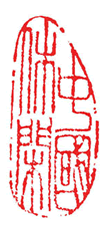张中行先生走了
——悼中行老
马惠娣
(2006年3月3日)
昨天上午十时,数百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最后看望了中行老。这位在风雨中走过98个年头的老先生安卧在鲜花丛中,还是那么安详、平和,像是在沉睡中。
我是从昆明出差回来才听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怕此消息有误,便打通先生家的电话。他的大女儿证实了并告诉我3月1日中央电视台早晨7点钟《东方时空》栏目将播出有关先生的专题片,还告知3月2日上午10点在八宝山举行告别。
我的思绪有点乱,甚至突然感到某种迷茫。
连日来,站立在我家专放先生书作的书柜前,一本一本翻阅他送与我的那些书,往事也一一出现在眼前。
我与先生相识于1991年。那时我正在帮于光远先生搜集有关对所谓《易经》研究新发现——什么从《易经》中可以解读64个遗传密码、计算机的发明是来自《易经》等资料。于先生希望我多找资料,以便回击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论证。我不懂《易经》,自觉得这个任务完成起来有困难。因此,读书看报就特别留意这方面的文章。
恰巧这时在报纸上(《文汇报》?)读到张中行先生的一篇关于“《易经》中不存在现代科学” 的文章(文章确切的题目记不清了)。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并邀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11公寓(?)——他的女儿的家一叙。(那时,他还没有自己拥有的居所)
我们一见如故。有关《易经》中不存在现代科学的问题,他谈了很多,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学识十分渊博,所述观点往往是一语中的,很深刻、很尖锐,但平和的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叙述的气质传递出一耿介书生的真与执拗。
临别时他取出《负暄续话》一册,并在扉页上签写了“择本 马惠娣女士指正 张中行 九一年九月”。
告别的时候他执意要把我送出来。我记得我们在朗润园走了一圈,好象还走到了未名湖畔。先生边走边向我讲起了老北大的人和事。1991年秋天的朗润园美丽、清澈、宁静。
此后,我们不断地有来往。我去他的家,他也到我家来。每次他出版的新书都赠予我,每次在扉页上他都为我签了字。
我曾随他去河北香河的老家,他讲述那里的故事,探访记忆中的那座塔、那架小桥,以及静静流淌的河。他说,他的青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他喜欢吃香河肉饼、小米粥,这儿做的地道!
他喜欢讲老北大的故事,他与我讲过胡适、俞平伯、辜鸿铭等,讲过红楼的哪一侧门前有一个烧饼铺。
他喜欢砚台,有时他会从柜子里拿出那些“宝贝”给我看,给我讲解。我记得有一块砚是宋代年间的。他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当他在西单商场发现这块砚台时,20元钱他都拿不出来,但是,他太喜欢了,最终还是把它买回来了。关于砚台典故,先生知道的很多,常常向我讲起来。
知道先生识砚,我和丈夫决定请他帮助我们买一方。那年(大概96年或97年)他帮我们在当时开在南池子皇史城中的“名砚斋”相中一块大约20厘米厚、60厘米长、40厘米宽的大歙砚一方,价格不菲。先生说,老坑的歙砚可能基本没有了,这块可能是最后的作品。先生还说,这块砚的形态以及雕工都古朴、自然。我们当即买了下来。遗憾的是,几次想请先生写一个“砚文”,但觉得太劳先生的大驾,最终也没有向先生提出。
又是哪一年(大概95年或96年?)他已经搬到了祁家豁子的华严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备了一幅写好的字给我。总共四句,宣纸2尺盈余,中楷行书。送给我时,他特意装进了一个信封里。然后他嘱我说,如你要裱糊,可到琉璃厂的“荣宝斋”,找萨本了(?)先生,告诉他是我让你来找他。先生赐予墨宝与我,让我喜出望外。回来后反复观之、赏之。
他书房中的那个旧的八仙桌,是先生每日伏案写作的地方,是他沉寂思考的地方。他习惯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张的格子纸写作,一字一格。每个字都那么认真、端正,独具魅力。文章似乎都一气呵成,很少有改动,即使有改的地方也勾勒得清清楚楚。他不满有人改他的稿子,他说,常常被改错了。因此,用他的稿子是不许被改的。如果要改,那他宁可不发。
他后来搬到华严里的寓所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给他的。三室一厅,水泥的地面,白灰的墙体,没有任何装修。他说,这样挺好。室内的家什大多普通,但他的八仙桌、书柜(好象八仙桌上还有一个宋代某人的手书真迹)都有点历史。
他的饮食也很简单。粗粮杂食是他喜欢的。他告诉我,他喜欢喝点酒,不需要丰盛的菜肴。可不是吗,他家的门旁有时的确堆了酒瓶子。后来只要我去探他,就带上一瓶茅台酒。他会批评我,这是奢华。但他还会说,茅台酒当然是好酒,留着和朋友一块喝。前几年他嘱我千万不要再带了,他已经很少喝了。
他喜欢京剧。但我没听他唱过。我告诉他,我也喜欢京剧。他很高兴,便跟我聊起了梨园的逸事。他推崇刘曾复先生,说这位清华大学学理工的,对京剧、京剧史的研究功力相当深厚,是京剧研究大家。大概是1997年的秋季,先生带着我来到当年的名伶梁小鸾家里(东总布胡同东北角的路口处,现在已无踪影),同来的还有刘曾复先生、故宫博物院的朱家缙先生。梁小鸾早年师承王瑶卿,后又拜梅兰芳,曾与谭富英、李多奎、金少山等同台演出,红极一时。那个下午,已是近80岁的梁先生清唱了几段,然后又欣赏了她当年演出时留下的录音。先生嘱梁小鸾送她的《我与京剧艺术》书一册与我。
1998年的春节先生还把梁先生、刘先生请到我的寒舍与于光远夫妇、陈鲁直夫妇(后来成思危主席也来了)相识、相聚,共叙友情。后来先生与于光远多有交往,偶尔会小聚在一起。
他喜欢读书,而且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习惯。他说,他不会做家务,得宜于有贤妻。(我认识师母时,她已年逾80岁。人娇小,背部有点驼。她仍留有旧时女人的风范——贤淑、温良、大家闺秀。后来她患脑萎缩,每次见我去,总会说同样一句话:“你总也没来,怪想你的”,然后会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师母给我留下了美好和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那淡然的笑、那妥帖的举止,对先生的成就也是一种辅佐。)
他的书房里有几柜子旧书,都是他青少年时代和大学期间阅读过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学语言文学的才子,也读彭加勒、罗素、洛克、卢克莱修、蔼理士等大量西方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好多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受到这些书的影响。他的床上靠墙一侧和床头都放满了书。读书、写作是他平生最喜欢做的事。
我的手头存有一本《有闲阶级论》,是1995年的中秋节我去看他时,他得知我正跟于光远先生研究休闲问题,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先生旧书中的一本,从扉页的签字看,“民国28年3月17日托子明由局拿来”,还写了“人间奇书之一,中行”。我曾问先生,如何理解此书是奇书之一?我记得他说,西洋人的学问很深刻,把富人阶层剖析的淋漓尽致。这本书虽然又经商务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过,但我始终没有买到新版本。所以当我还他书时,他说,这本书就留在你手里吧,反正我不会再读它了。
在先生众多的弟子中,徐秀珊颇得先生的赏识。90年代中期,我在先生的引见下,与徐有两次谋面。她小我几岁,人很质朴,性谦卑文雅。先生评价她认真、勤奋、刻苦,曾经在北京电视大学学中文。那个时候她正协助先生编《说梦楼谈屑》,并为之写下了“编后小言”,其文风、语气、禀性很接近先生。
我曾见过多位先生的朋友,而先生的朋友们大多像先生的为人与气质,是先生影响了他们?还是“人以群分”?我常寻思着。
最后见到先生是2005年的3月。上海作家红舒来京邀我和作家协会的张素英一同前往先生的家。那天是两个阿姨把他从床上扶起。大家围坐在床边与他聊东聊西。记得他还出了个对子,还评论了郭沫若的《申甲三百年》,还说到了柳如是。我们与他合影留念。张素英还给他带去了文联付给他的稿费。大家打趣地说,先生得请客才是。他也笑应着“我请客”。
……
先生的一生的确未曾“逐鹿中原”,未曾“惊天动地”。但他的骨子里始终是“思想澎湃”,“一种入骨的,是以大智慧观照世间”(“自嘲”篇)。他的书、他的字、他的词、他的做、他的行中凝聚了“八百里湖光,奔来眼底;十万家忧乐,涌上心头”,“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月夜;六朝花柳,几无隙地种桑麻”的情与思。
他散淡中透着执着,儒雅中透着傲骨,平淡中透着轩昂,随意中透着严谨,庄重中透着诙谐。这是先生的魅力和感染力。
先生总是自称“平庸之人”。他在《流年碎影》的扉页上写下这样的字句:“自然,人有大小,事有大小,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而在此书的“住笔小记”上又写到:“我人平庸,经历也平庸,未曾中原逐鹿,也就写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然,其他的书中他也是这样自遣自己。
正是他的“平”与“庸”,留下一个“淡泊明智、宁静致远的“负暄翁”。对于先生的“淡”,徐秀珊女士在《桑榆自语》一书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淡是平实,质朴,无金粉气。味是耐咀嚼,可以再思三思。这种“淡而腴”的味道,我以为不仅关乎他的行文风格,而且与他的人生态度有关。”
先生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我以为,先生喜欢“负暄”,追求负暄。他以“负暄”为题完成三本书,即:《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既使《桑榆自语》、《流年碎影》、《说梦草》、《禅中说禅》等,不也是在“负日之暄”的境界中吗!
先生的“负日之暄”是怎样的境界?——“找个心爱的安静地方结庐,门外看流云,门内理残籍。枕上,春日听啼莺,秋日听蟋蟀。如此,数晨夕,尽余年。如有机缘,我将选择哪里呢?……”(见先生《通州怀往》)
负暄翁走了,在“负暄“处结庐。那里必是春风融融,阳光沐浴。
|